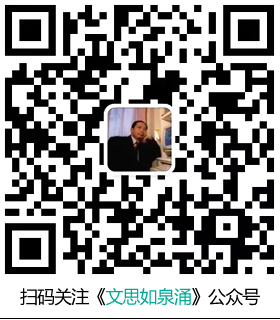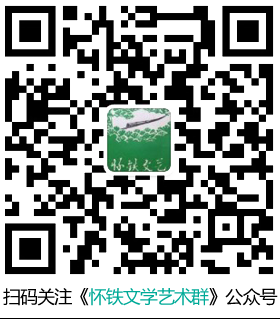母 亲
母亲素来的眼神是那么安祥,那么宁静,我在子夜的功态中,是融进了母亲的眼神中去了的,正如月光融进了水里一样。

我的母亲余之明
岁月悄悄流逝,流逝的岁月也曾带走过母亲几回异样的眼神。当母亲怀第七胎的时候,她的眼神是显得那么焦躁不安,她埋怨这个小生命的形成;她担心养不活他(她),因为有两个孩子先后夭折了。于是眼神的焦躁变成拳头暴躁,她拼命地去击打着腹部;有意作剧烈的运动,想将腹中胎儿流掉。据讲,她还弄了一些堕胎的药吃。然而,母腹中的这个超乎寻常的小生命,在1953年11月9 日的晚上,伴随着阴冷阴冷的寒风;伴随着懒洋洋的雪花,提早来到了人间。婴儿的哭啼声挺有气度;婴儿的哭啼声唤醒了母爱,母亲将他紧紧地搂在怀里,从此便用整个心血去养育着他……
这个孩子便是我。

孩提时的我与两个姐姐合影
十岁的时候,我清楚的记得那天晚上很闷热,那是春天将要咬住夏天尾巴的季节,母亲坐在父亲床边,眼神明显流露出恐慌的神情,父亲有气无力的躺着,脸色腊黄腊黄,他患有肺病,平常体质就较虚弱,前几天,防疫站的人来这里打什么预防针。直觉告诉他,这种预防针不能够打,但父亲的建议没有采纳,医生还是带强制性的给他打了预防针。上午打的针,下午他在县里开政协会就坐不住了,回来往床上一躺就再也起不来了。只几天时间他眼睛都窝进去了。他向母亲摆了摆手,双唇颤颤喝了点汤,剩余的罐头示意留给明天吃。那知次日清晨,他已说不出话,手不停地比划着。母亲弄糊涂了,不知他要干什么。精明的二姐会意,赶快端来药。药还没送到他嘴边,就断气了。当时我正在楼上玩,我听到母亲的哭声,知道父亲死了,挺害怕。我在暗暗流泪,好一阵子,母亲上楼来了,她望着我,眼神是木纳纳的,她与父亲找了一身好衣服便下楼去了。
父亲求生愿望很强,病情再严重,他也避而不谈一个“死”字。能够起床,便习惯坐到外面去晒太阳,看报纸,精神再好点就上山去弄些柴来烧。他是大学生,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。三十年代,他抱着虔诚的宗教信仰,带着母亲从长沙来到修水,自己却被肺病折磨得够呛,他六十二岁病故。母亲拿了一张黄纸将父亲的脸盖上,木纳纳的眼神便又与那张黄纸融在一起。
二十年后,母亲病瘫在床。晚上起来解手不慎滑了一跤,便再也站立不起来。她是虔诚的基督教徒;是父亲的学生。每顿饭前她都要祈祷几分钟,请求上帝保佑全家人的平安。她在病瘫期间,眼神蕴含着强烈的求生欲望,那目光我总不忍看。她送给我一本《新约全书》,她在疾病缠身的晚期,一再叮嘱我要信仰上帝。提到上帝,她的眼神又变得安祥起来。上帝的信徒都是这种特有的安祥眼神么?她躺在床上痛苦万分时,也曾多次呼唤着上帝。 父母生前还常唱道“感谢上帝,万福之根……”令我困惑不解的是:“上帝”为什么无动于衷? “万能的主”到哪里去了?怎么能忍心让他忠实的信徒在疾病中煎熬呢?!
母亲静静的躺在故土,已经整整十年,这些天,她那安祥的眼睛老象在望着我,目光透进我的灵魂深处,不能再耽搁了,工作再紧也得设法回故乡去一趟,该与母亲扫墓了!

妻子在扫墓,旁边为我小孩,左为细水
九四年八月,我带着老婆、孩子终于启程了。我的故乡在江西修水县,那里是个大山区,至今没通火车。路途太远,搭车不便,加上工作又忙,是我一晃隔了八年没回故乡的主要原因。母亲也正是在十年前的八月病故的。邻居学义告诉我:“我看了表,她是二十五日晚上十点三十三分落的气……”故乡只有大姐送她的终。除大姐外,我们四姊妹都在外地工作,母亲死后的第三年,大姐也随同姐夫调苏州工作了。如今只剩下母亲孤零零的在故土安息。好心的邻居便建议我们选个好日子,将母亲的坟迁走。与我二哥同辈的孙学寿是故乡烟草公司经理。他和他妈妈一样,好做善事,助人为乐,活动能力又极强。在我们那片邻居中,他们母子都是“领袖”式的人物,有较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。那次我回故乡去,他对我说:“不要紧,到时候迁坟时我将怀保请来帮忙。我们带个炭盆上山,将你娘的骨头烧成灰,装进骨灰盒你们再带走。关键是,这里你们没有一个人了……”“迁坟方案”我们起初认为可行,并在母亲诞生的故土湖南长沙县的一个乡下选了一块地,准备将母亲的坟迁往那,那里还有我们的姨妈和舅舅。后来,我们五姊妹反复商议,又认为“迁坟方案”不可行,母亲还是安息在她的第二故乡好。主要有这么几个因素:一、母亲虽然是湖南人,但她真正的根在修水,她在这里生活了五十多年,直至去世。她与左邻右舍建立了深厚的感情,就是在她的坟周围都安葬着不少她生前挺要好的人,这里到处都充满了她倍感亲切的信息。从这个意义来讲,她在修水安息并不孤独。二、她真正的老家,她反倒感到陌生,亲戚之间平时联系也极少,她在世时,到我们这里来玩都呆不习惯。她形象地说,呆在我们这里象关鸡,邻居之间都不来往。以此推理,将她迁到一个“陌生”的地方去,她的灵魂能安息么?三、母亲生前最怕火葬, 她之所以不愿到我们这里过老,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。安葬母亲时,又是根据湖南人的风俗带永久性的,坟坑比故乡的要深一半,下葬后再用“三合土”封棺。现在又要挖开将遗体烧灰,我们也实在不忍心。五、母亲的坟在故土,这样还会促使我们这些远方的游子寻根。六、父亲是六三年去世的,“文革”期间那片坟地搞基建,正是“破四旧”的风口上。房子的地基平整好了,我们才知道父亲的坟毁了。如今母亲的坟我们五姊妹不约而同发出同一呼声:一定要保存好!
八年前,我回故乡住大姐家,那阵子,他们正在忙着搞调动。今年我是决定去扫墓的,但原计划是十月份以后,我独自去。主要是路途太远,要转两次火车,还要乘整整八个小时的汽车。这一次一家子出动走得非常突然。孩子正放暑假,爱人又恰这个月休公休假。于是,我们便临时决定,一家人奔修水扫墓。孩子最后一次见到奶奶,是他奶奶去世的时候,那时他才一岁多。母亲入棺后,我们抱着孩子,让他看了奶奶最后一眼。整整十年啦,母亲在九泉之下,不也盼煞了她的孙子么?不过, 我们这一家子浩浩荡荡回故乡,在没与那里的人事先联系好的情况下,到哪里落脚呢?是住旅社,还是直奔邻居家?究竟又到哪位邻居家?我们一路都在酝酿, 我不由想到了我的一位最亲密的朋友——
细水是乳名,他真名叫龚水生。细水比我年纪大,与我二姐是同辈人。一般来讲,他应该在他那个年轮的水平线上交朋结友。没想到,我还在读小学的时候,这个“中学生”却毫无架子的混进了我们的队伍里。我们一起上包公岭砍柴,小伙伴都喊他“细水”,喊得怪甜。他性情也恰似细细的溪流,静静的清泉。为人忠诚,心底透亮,与世无争。母亲生前对细水的印象极好,常夸他这个人温温存存,不惹事生非,将来会有大的出息。72年我从修水共大分校毕业后,分在故乡三都茶场工作,细水则比我来得早,已在一个工区的食堂搞管理。后来,我到了场部任文书,我们关系更亲密了。我这时才偶尔发现,他有一手挺漂亮的隶书字。我搞文书时,时常请他来帮着抄抄写写,他们工区打牙祭,每次也都忘不了请我去“赴宴”。参加工作前,我们还有个地方相见得最多,那便是在“刘家井”边,我们象有什么心灵感应似的。他去挑水,我来了;我到井边,又遇上了他。他们家离井边近,我们家却远得多。我们挑水回家要经过一个巷子,巷子的入口处住着几户人家。其中一户的人家的一位姑娘最爱望着我们挑水出来。这位姑娘就是细水现在的妻子。
我们这次回故乡扫墓,从九江下火车时,天气热得象炸开了锅。但当汽车奔驰在故土上,情况起了变化,气温明显的降下来。车子快开进县城时,还刮起阵阵凉风,下起小雨来。细水如今在县公安局秘书科工作,我们很顺利的找到了他家。那是一栋旧平房,房子挺宽敞,后面还有一个可观的院子。屋内谈不上豪华,但收拾的非常整洁。给人一种舒服,明快的印象。细水莫是心灵感应到了我们会来么?细水的妻子是典型的“贤妻良母”型, 我们的到来,她神情是兴奋的、欣喜的、亲热的。她象一个乐团的女指挥,以她那家庭主妇的特有风采,一边唤着孩儿们做他们该做的事;一边忙着给我们烧水洗澡;忙着做饭弄菜,利利索索,将我们安排好,她这才长长透了口气:“你姆妈是个难得的大好人哟!”她冲着我们这么说。 “细水也总提起你娘,你们隔得远,我们一家经常到她坟上去看的……”

妻子在扫墓,旁边为我小孩,左为细水
故乡的人确实情深大义,不仅仅是他们经常去看我母亲的坟,还有好些左邻右舍。由于路途遥远,我们很难回一趟故乡。我们对面的匡英义,他是县林业部门的干部,就抽空常看我母亲的坟,清明时节还代我们去帮母亲扫墓……
细水的爱人在县中医院上班。
细水本来是极勤快的人,婚后想必已退居“二线”,在厨房里“冲锋陷阵”的几乎都是他的妻子。只是他向我们露了一手“煎鱼”,那可称得上是中国一绝。至少,我跑了大半个中国,还没有吃过象他弄出来的那般鲜嫩可口的鱼。鱼里面不知弄了些什么佐料,我只知道还有百合的香味。细水有两个男孩,老大叫健健,在读中学。小的那个叫龙龙,在读学前班。龙龙非常非常聪明伶俐,尤其是那张嘴巴乖。他跟我说,他爸爸不叫“细水”,他才是“细水”,他哥哥是“大水”,而爸爸呢?是“老水”。 是的,我们都进入了不惑之年,不可回避,那个令人讨厌而又心酸的“老”字,已明晃晃地亮在我们前头。细水还是老样子,只是微微发了些福。他爱人却仍在“姑娘”与“妇人”的界限中挣扎。从她的笑声中,还能引串出她当年少女的影子。
我们回故乡,县城变了大样。往日显得气派的三层楼商场,如今显得格外破旧、矮小,它斜对面拔地而起的邮电大楼却是十足的城市气派。好些房屋拆了,盖起了新楼,形成了新的街道。这里浓厚的人情味却没有变,我爱人是四川重庆人,连夸“这里人真好!真好!”她表示下次还争取来。的确,左邻右舍见我们来,惊喜的声声叹息:“隔久了,隔得太久了!我们总是念着你们呢!”八十多岁的“一嫂”妈妈硬要塞给我们十块钱,不收下还不行,讲是送给小孩的;万妈妈也塞过来二十块;英义、晶晶两家又忙着请我们去吃饭;与我一起长大的学清则由她领着我们去参观黄庭坚纪念馆;余妈送来了故乡泡茶的特产、菊花、芝麻、黄豆、咸萝卜……万万没有想到,原来住在我们隔壁的那位名叫万长菊的同学,也赶来塞进我口袋二十元钱……她原在班里长得最漂亮,如今她少女时代的风韵,出神入化地传给了她的女儿……
第二天,细水便带着我们上山了。朝母亲的坟边走去……
母亲起初能弯着腰扶着墙,慢慢地往前移动。后来步子越发艰难,往前挪步,腰弯到了不能再弯的程度;我们只有请人来照料她。她不显老,七十一岁了,还有一头溜青的令人羡慕的头发。她思维清晰,一面虔诚的信仰上帝,一面热心地关心着国家大事。她爱看报,她曾当选过学习毛zhu席著作的积极分子。我们回家探亲,往往还没到假期,她就变着法子催我们回单位上班,她说搭车不方便,万一没赶上火车怎么办? 还是提早点走保险……她那较高的政治觉悟,与那执着的宗教信仰,有机地融到了一起。到了晚年,尤其是这次病魔缠身时,她那执着的潜在的宗教信仰逐渐公开化。她病瘫期间,能吃健谈,精神挺好。只是病情时而恶化,时而又化险为夷。她病情稳定时,多想去串串门,上街走走呵! 有时她是悄悄地移到了屋门口的,但终究不能迈出门去……令人心酸的是,她有过那么几回“病危”,后事都料理好了。那知我们几姊妹千里迢迢赶回去,她偏偏又“起死回生”,病魔继续折磨她……
那天我临行前,刚迈出家门,突然母亲爆发出悲怆凄切的声音:
“好好走呵!我是不能来送你呵,崽呀……”
我的心碎了!我转身进屋帮母亲擦干满脸的泪水, 我已经预感到,这是最后一次;最后一次了!三个月后, 那是一个星期天,工厂的向师傅一次给我送来两封电报,一封写着“母病危速回”,另一封则是“加急”的,跳跃在我眼前的那行字令人心碎——“母死速回”。这是八四年八月二十六日。
母亲病瘫了整整两年,是活活“闷死”的。那天晚上,您要起来解手, 您不敢大声喊,您怕惊醒远道而来看您的我们。您细声唤着睡在您身旁的那位;我们请来照料您的姑娘,您唤了好些声好些声,她都没醒。您声声呼唤,在猛烈敲击着我的心呵! 我听不下去了,您那呼唤声激起了我的愤怒!那姑娘可受不了, 马上提出要走。您狠狠责备了我,您说人家家境不好,我们不能见人贫寒就欺负她。我只有向她道歉,我又想塞些钱给她,被她坚决拒绝。她也有她的苦衷,她说母亲晚上要起来好多回,这一次她是瞌睡来了。她还向我保证,往后她会警醒些,不脱衣睡,讲得我鼻子早酸了……
母亲的声音总是那么能震憾我的心灵,我不由想起了一桩往事:
柴砍得多,又舍不得丢掉,勇士般地瞧瞧自己的担子,挥手冲着小伙伴说:
“你们只管先走!”
“那,我们回去叫你妈来……”
“哈哈,他妈能接柴?恐怕空手进山都为难呢!”
的确,那阵子家里就只剩我和母亲了,哥哥和姐姐都远离故乡,有的已参加工作,有的正在读大学。母亲年老体弱,脚比正常人的小,这是患风湿病闹下的。
“你贪心罗,看你能磨回家!”
一个小伙伴回头冲着我笑骂一句。
起初我还耐得住,上岭后距离就拉大了! 咬牙熬到岭上,不得不放下担子,眼巴巴地望着小伙伴奔下岭去……
没有一丝风,日头象要把人榨干,喉咙管仿佛在冒烟!然而,岭下是白晃晃的大路;岭下似乎离太阳远得多;岭下有诱人的樟树林;岭下还有清凉的泉水……
水……水……
岭下成了美好的希望,希望给人的潜力送来了个惊叹号!粗气喘喘,担子又上肩……
下岭比上岭足足远一半路,肩上的担子也仿佛轻了一半。虽说腿脚飘颤、打跪,但终是下完岭,痛痛快快饱饮了一肚子泉水。舒舒服服躺在大树下。烈日不再显得可怕。清泉失去了它应有的魔力。
该上路了,腹中隐隐觉着有啥东西在钻。
太阳渐渐偏西,人实在是精疲力竭了,可离家还有五六里,母亲这时该多么焦急呵!
“光林——是你吧!”
天啦,是母亲的声音!她怎么来了?!母亲说, 我平时都回得早,今天却落在别人后头,很急。她担心我饿坏,又怕我在途中摔跤,吃罢中饭就慌慌张张地奔进山来了。她走错了路,走了许久许久,才听一名乡下人说,那儿已封山育林,城里人砍柴不会到那去的……母亲含着笑,讲这些,象在讲一个美好的神话故事。我心底荡漾着一股暖流,脸上却添了几分怒气!怨她不该来接我, 我不愿吃她送的饭。
“吃吧,吃了能增点劲呀!”她慈祥地望着我笑。
我开始狼吞虎咽地吃,她也开始嗔怪我不该这么称雄,怕我担多了闪了腰。
肚子饱了,母爱赶走了疲惫,担子也显得轻。
“你放下,让我试试!怕也能挑得起呢。 你歇几步也是好的呀。”
我被她这一激,步了迈得更欢了!
“哈哈!慢点慢点,莫绊了跤!”
后面,又传来母亲的声音……
母亲这声音浸进了我的深层意识,至今这段话老在我耳旁回荡。伴随着母亲的声音练功,我明显感到身上气感的增强;自己功力的提高。是的,母爱也是一种能量。母亲不仅对我充满了爱,她还把她的爱,变极放大扩散到生活的空间。在人们心中形成一种场能;一种“爱”的特有氛围。
人世间,有些道理要许久才会明白。
我曾是那么地埋怨母亲,埋怨她老人家人情味重,手头有点什么总爱送人。有桩事对我感触很深,那还是我做梦都想当红卫兵的时候——
店里来了一批部队转下的解放鞋,母亲也挤在人群中兴奋地替我买了一双。鞋子是38码的,当时穿不得,只有压在箱底留待明年穿。哪知第二年开箱,鞋子不冀而飞了!我火爆爆地冲着母亲问:
“妈!我那双解放鞋呢?”
她笑了笑,还是那句话:
“送人了。”
“谁?”
“唉,乡下人进城卖柴作孽!那么冷的天还打着赤脚,走到城门口就被碎破璃戳一下,流了好多血……”
“那就该将新鞋送人?!”
“别这样大声嚷!大家也是很懂情义的。后来, 她还送了只大野鸡来……”
“那,鸡呢?”
“刘嫂对我们那么好,她坐月子需要补,没啥好送的,就给了她……”
我还能说什么呢?
妈妈呀!妈妈!您请人杀只鸡,也要煮几个荷包蛋去答谢;陌生的山民穿得破,您慷慨地送给人家衣服;连3 岁的小孩子到我们家来玩,您也象对待大人那般,恭恭敬敬泡上一小杯茶……然而,您自己却省吃俭用,一点剩饭煮些白菜就能将就解决一餐;那件青布衣旧得不成样子了,总不肯添做新的……
现在,我渐渐醒悟到:如果人人都象母亲那样,这个世界将会变得美好得多!
我不由又回到我的童年——
太诱惑人了!冰棒那时候还是新鲜玩艺儿, 每逢盯着人家吃,口水免不了在喉咙管边滚动。望慌了心,竟冒冒失失去讨:
“那点给我吧?叔叔,你,想吃不想吃的样……”
好多次,大人都慷慨地给了。只有那么一回,我话还没说完,脸上就火辣辣的挨了一下。
母亲心底象抹了蜜,嘴角常挂着笑。她喜滋滋地告诉我,那么多临时工都回去了,就她一个人留茶厂,这是党对我们家的恩!

我小孩来看他的奶奶
“一个月挣27块,解决大问题呐!”她压低嗓门, 要我别张扬出去。“工作呢,没有定死的任务,只是补补破布袋,全靠自觉!”
我没心思听,仍在欣赏浩浩荡荡的蚂蚁搬家。母亲叹气道:
“你父亲死得早,要懂点事呀!读五年级的人了, 还惹蚂蚁!你哥哥姐姐哪象你!”
有一阵子,她冲着我神秘一笑。待我睁圆眼睛,她才将那令人鼓舞一消息公布出来:
“暑假在这里好好玩,保证一天给你买支冰棒!”
蚂蚁拖苍蝇,苍蝇背上压石块,尝试了许多回仍拖不动,只好回洞搬救兵……玩兴正浓,母亲一把将我拉出:
“来,干点正经事!学着补布袋, 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!”
我在一堆破布袋中,仔细挑选出一个洞眼最少的。没想到母亲脸一沉,向我投来责备的目光:
“人,不要学着奸滑!”
我脸一阵发烧,继而挑出一个最破的,仔细地补好,完全 符合质量要求。这下她乐了, 当透着茶香的热风送来“冰棒,牛奶冰棒”的吆喝声时,她赶快奔出外,一下买来两支:
“呶,奖给你!……”
84年8月27日零点,是我终生难忘的时刻, 母亲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入棺,我们分别向她老人家的遗体告别,左邻右舍也排着长长的队伍,一个接一个地在母亲的棺前跪拜磕头……
母亲生于1918年8月4日,死于1984年8月25日。享年66岁。

细水带我们来到母亲坟边,前两年我汇了些钱来,托他将母亲的坟修整、硬化一下。坟修整得令我们满意。坟上就不会长草了。毕竟太远了,我们几姊妹不可能经常来扫墓。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,这个地方的环境变了。八年前,这座山似乎毛草都挺少,一座座坟墓则格外刺目,给人一种悲凉的景象。这次来,恰似进入一个森林公园,四周的松树都长大了,草也长得格外茂盛,细水在前面奋力开路,才将我们带到母亲的坟边,母亲的坟四周一片葱葱翠翠,煞似羡人。
“妈妈,我们看您来了……”
“奶奶,我看您来了……”
我们一一告慰了母亲之后,我便盘腿坐在母亲的坟头,开始在陪伴着她,我把对母亲深沉的爱,伴随着体内真气的运行,融进四周清凉的空气中,浸进这片热土上……

 相关文章
相关文章

 排行榜
排行榜
 编辑推荐
编辑推荐
 关注钟奋生
关注钟奋生